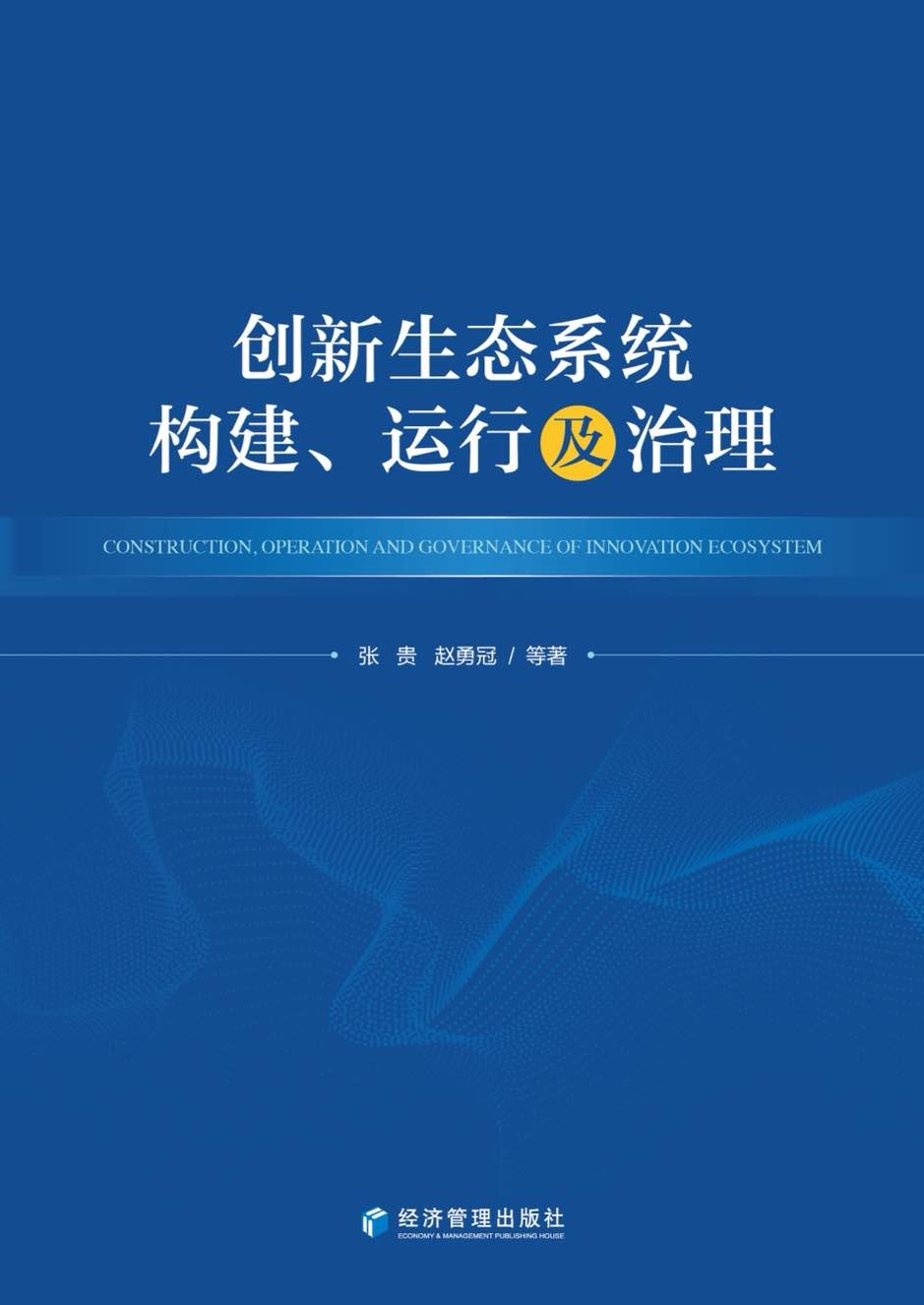【内容简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各种机遇与挑战交织并存。在此背景下,构建以强大科技创新能力为基础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创新生态系统的兴起,反映出国际科技创新范式的深刻变革,在企业和市场之间形成了第三种创新治理机制,促使全球科技竞争逐步向不同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转变。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促进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对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战略意义。
本书从国家竞争优势视角出发,以“创新生态系统2.0”理论框架为主线,在阐明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原理基础上,重点聚焦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运行和治理机制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围绕系统中“核”企业的演化、创新生态位的进化、创新枢纽城市的产生、系统韧性等重要主题展开探讨,并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进行了三维量化评价分析,从而深度展现“创新生态系统2.0”的理论创新成果,以期更好回答创新何以发生、如何产生等重要问题。
本书强调创新要素流动既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又是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的内在动力。在构建“双循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中,创新要素面临重大调整、升级、完善和优化等新要求,本书聚焦知识、人才、数据、高铁等创新的新要素的流动模式,基于耦合协同等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创新要素促使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培育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新优势。
本书提出创新生态系统2.0概念及相关理论,这是对经典创新生态系统(1.0版)的重大修正。“创新生态系统1.0”是对Moore的“商业生态系统”、Adner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Adner和Kapoor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等经典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总称。“2.0版”在前者的基础上,对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创新条件和创新环境作出了重大修正,强调要素的结构和功能,重视依托输入性创新基因孕育和培植原生创新,明确了创新生态系统是以具有竞争优势转型能力的企业为系统“核”、多元主体参与、多种创新方式并进、多维网络化协同治理、以产业生态化为取向、以绿色发展为约束的复杂适应性系统。
本书认为,创新生态系统2.0是以实现特定价值主张为核心的主体聚类与政策体系集合,是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创新条件和创新环境的统一体。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自我组织效应、协同进化效应、平台赋能效应和价值共创效应,最终形成价值创造的“闭环”。在一系列驱动因素的非线性叠加作用下,创新生态系统遵循着“创新源—创新组织—创新物种—创新种群—创新群落—创新网络—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路径,并呈现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转型期”的演化路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企业、产业、城市、区域和国家五大层次,不同层次的系统逐层嵌套、相互关联,造就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多元化特点。
创新生态系统2.0具有五种构建与运行机制,分别是竞合与共生、扩散与捕获、催化与涌现、学习与反哺、开放与共享,它们共同构成了创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基石。其中,竞合与共生机制注重创新主体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借鉴,是系统建构的关键;扩散与捕获机制强调激活创新成果在主体间的流动,是系统从孕育到成熟的基本要求;催化与涌现机制注重对创新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是系统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过程;学习与反哺机制旨在提升创新主体的知识运用和知识创造能力,是系统充满活力、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开放与共享机制有利于扩展创新资源的来源和范围,是系统良性循环的必备品质。
创新生态系统2.0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完备的治理机制。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以多中心治理框架为内核,包括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两类机制。正式治理机制主要通过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治理力量,保障不同创新主体间合作、竞争、交易等关系的公平有序;非正式治理则通过信任、声誉、创新文化和联合惩戒等治理方式,引导创新主体在复杂多样的创新环境中实现合作。实践中,伙伴选择、激励相容、利益分配是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的典型应用场景。此外,创新生态系统治理还需关注平台化治理、网络化治理和数字化治理等新兴方向,着力提升系统的治理效能。
创新生态系统2.0的“核”是具有竞争优势转型能力的企业。这种“核”企业的生命周期分为初创期、扩张期和成熟期,分别对应不同的创新生态战略。初创期企业主要采用外部生态系统依附战略,重在形成孵化生长优势;扩张期企业的战略选择会升级为架构主导战略,注重培育共生整合优势;成熟期企业的战略选择进一步升级为变革演化战略,由此形成变革再造优势。创新生态系统以“核”企业的战略优势塑造为中心,聚焦创新范式变革引发的组织情境、创新基因培育所需的环境情境、技术更新迭代所引导的产业情境等维度,统筹系统的创新协同、创新支持、创新变革功能,从而实现动态演化与转型升级。
在创新生态系统2.0中,“生态位”集中体现了创新主体的地位与优势,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逻辑起点。城市作为创新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其生态位包括状态、功能和关系三个维度,分别对应生态位的宽度、强度和重叠度。不同类型的城市生态位对应不同的城市竞争策略:处于“明星类”生态位的城市应采取巩固提升策略,处于“金牛类”生态位的城市应采取选择变异策略,处于“中等类”生态位的城市应采取适应调整策略,处于“幼童类”生态位的城市应采取协同进化策略,处于“瘦狗类”生态位的城市需采取延伸优化策略。
在协同创新背景下,创新枢纽城市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创新枢纽城市是我国区域内部综合实力强劲、科技创新研发领先并能够辐射带动区域内其他城市发展的创新优势区,是区域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知识网络、创新网络等多网络交汇形成的综合性枢纽。它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产业集群为基础,以集聚扩散为表现,具有集聚性、扩散性、网络性、平台性和生态性特征,能够为区域乃至全国创新体系输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技术、产品、服务等。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的演化是创新枢纽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规模效应、集聚效应、结构效应和生态效应,促进创新枢纽城市的创新能力提升。
面对创新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升创新生态系统的韧性至关重要。韧性是创新生态系统在面对内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扰动风险时,通过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系统记忆等方式恢复到更高功能水平的能力。它由抵御能力、吸收能力、组织重构与系统更新四种能力构成,具有多样性、进化性、流动性、缓冲性、网络性的基本特征。系统韧性在演化过程中存在韧性演化失败、韧性演化依赖和韧性演化成功三种路径,其中韧性演化成功需要一定条件下的高韧性和高冲击。系统韧性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发展。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以成长性、活跃性、适宜性为关键特征,依据这些特征构建的城市创新生态指数有助于全方位刻画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水平。基于我国创新型城市数据的评价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效显著:系统成长性持续提升,加快从系统形成期、快速成长期向缓速成长期和成熟稳定期演进;系统活跃性不断增强,在创新浓度、高度、活力度、治理度和响应度“五度”层面呈现“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的转型态势;系统适宜性稳步提高,对创新主体需求的满足能力进一步强化。实现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功能强化、结构优化,需要从各维度、诸方面统筹施策,注重把握不同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各类创新力量加以整合,最大限度激发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对“生态租金”的创造能力。
相对于本领域已有研究成果,本书的独到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构建了“创新生态系统2.0”理论框架,从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形成机制等方面丰富发展了经典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二是提炼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运行及治理机制,突出了多元化、共生化、网络化创新主体所形成的自组织、自适应能力;三是编制了城市创新生态指数,横向上有助于比较不同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发育水平,纵向上有助于判断系统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